
年 味

作者:李明洋


回老家
打小的时候,每年回乡下老家陪奶奶过年是一年中最庄重的事。爷爷过世得早,奶奶一个人独居在老屋里,犹如那时候还普遍照着的煤油灯,幽明而昏暗,摇晃着她的形单影只,也摇晃着她的茕茕孑立,将落寞过成习惯。
父亲是奶奶膝下五个子女中的老大,也是整个大家庭中唯一端着“铁饭碗”的工薪阶层,所以在每年腊月回老家的时候,他除了带上我和母亲之外,还大包小包地带着若干以供过年使用的物品,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带更多物品,父亲会把我和母亲当着了帮他驮运物品的人力使用,这种体验,直到后来乡下通车之后才得以解放。
翻过最后一个山头,就能眺见老家的房顶,以及院子里那棵枝叶婆娑的香樟树,一路行来的疲乏顿时被甩得干干净净。待得走近老屋,我会急喇喇地“奶奶,奶奶,我来了……”隔空欢叫数声,不一会,一间房屋的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,随即有一头花白头发以及头发下一额皱纹循声探了出来,接着有一双蹒跚的足迈出门槛,迎我张开双臂。

在我和父母到达老家后不久,二叔、小叔也带着他们各自的“队伍”相继聚拢而来,堂姐、堂弟们如似归巢的燕子,把我吸纳进他们的圈子里,像后来才有的央视春晚一样,我们七八个孩子有了每天的游戏节目彩排。接下来,一幅生动的情景逐日展开——父亲在燃着焦煤的泥炉上熬浆,准备张贴他早已写好带来的春联;小叔去寨外的井里担来满满一漉缸的井水,寓意“发财涨水”;二叔择日去邻村请来屠户,准备宰杀奶奶养了整一年的那头大肥猪;二婶泡好豆子、大米,然后在石磨上推磨出豆浆、米浆,准备做豆腐和粑粑;小婶去猪圈后的竹林里砍来几棵竹枝,做成一把长长的扫帚,打扫老屋各间屋子里的“扬尘”;母亲则招呼着我们这一夥小孩去菜地里拔了几大捆蔬菜,抱往村外的井水中洗净备用。

在一家人都积极地为过年做好铺垫之后,我悄悄问奶奶:“该杀猪了吧!”奶奶慈祥一笑,点了点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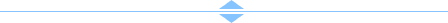
杀年猪
杀猪的那天,俨然是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典礼。先是二叔从厢房里扛出用于打谷子的戽斗置于院子里,二婶配合着奶奶把灶房里的两口大锅都烧满开水,屠户则一脸虔诚,在戽斗前焚烧了一堆香纸,然后震耳欲聋地放了一串鞭炮,夹杂着他口中念念有词,为即将开始的“杀生”进行祈祷。随即奶奶亲自去打开猪圈门,把大肥猪赶到院子,那猪大约是被方才爆炸的鞭炮声吵醒了它此生最后一场美梦,嘴里兀自哼哼唧唧地发着脾气。忽听得屠户一声暴喝,几条被请来帮忙的壮汉迅速将猪放翻按倒在戽斗上,待父亲刚把一个盆置于猪的颈项前时,说时迟那时快,屠户一把锋利的尖刀快捷地插进了猪的颈项,直没刀柄,刀子抽出后,殷红的血液喷射进父亲刚才放好的盆里,猪在戽斗上最后蹬了几腿,然后便静息下来,终于一动不动。
如果说杀猪是需要练就力气和胆气的“外家功”,那么接下来的“吹猪”则应该是一门“内气功”。杀好的猪横躺在戽斗上,屠户用一把小刀在它一只后腿皮下割一个小口,然后用一根长铁条伸了进去,在猪身的皮下和肌肉之间来回穿插,直至穿插完整头猪。接着屠户深吸几口气,将嘴巴对着已抽出长铁条那个口子往里吹气,边吹边指挥其他人用木棒拍击猪身,直到整头猪像气球一样被吹得膨胀起来,才用小绳将口子扎住使之不漏气。当然,这个比较考验屠户肺活量的“内气功”,在后来有了打气筒之后,这门功夫也就从此失传。

母亲与二婶、小婶鱼贯地将锅里烧开的水舀来,均匀地浇淋在吹胀了的猪身上,屠户换了一把比较宽长的刀,顺着热水浇淋的地方麻利地给猪刮尽体毛。须臾,一头雪白赤裸的大肥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,壮汉们用一个大铁钩钩在它的后腿上,倒悬垂挂在香樟树的粗枝上,屠户先把猪头卸下,然后开膛破肚摘出内脏。说起猪的内脏,最让我欢喜的是它的“尿脬”,我会央求屠户把它完好地剔摘出来,排尽尿液之后,屁颠屁颠地拧着它去冷灰坑中踩搓成薄薄的囊,然后去折一截竹管来把它吹胀当气球,能让我和堂弟们可以踢着它玩上好长一段时间。

待一切收拾得差不多之后,接下来便是奶奶的“定额分配”时间,她在心里暗自计算着她五个子女家人口的多少,以及寨子内外有多少亲密来往的长辈,奶奶会让屠户将猪肉分割成三五斤不等的若干“条方”,然后亲自分散给各家。就这样,一头大肥猪被奶奶毫不吝啬地分发殆尽,自己留下的肉则所剩无几,而且还得在过年期间拿来做成食材供一大家人吃,而奶奶最终只喝得几口肉汤,她也心满意足地说算是打了“牙祭”。
杀完猪的当天,能吃上第一口新鲜的肉叫做“刨汤肉”,血旺、猪肠、回锅肉等等七碗八碟自是丰盛无比,连同请来帮忙杀猪的屠户和其他壮汉们围炉而坐,被父亲及俩叔相劝着土法酿制的“包谷烧”酒,在欢声笑语中毫不隐晦地倾诉着这一年来的坎坷唏嘘,也相互祝福来年吉祥顺遂,就像他们那张吃着喝着的嘴,一并将酸甜苦辣滋味细细地品咂咀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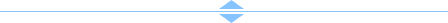
年夜饭
到了年三十这天,一大家子简单地吃罢早饭后,无论大人小孩尽都听命于奶奶的“指挥”,开始张罗着年夜饭。
要说做年夜饭的能手,非父亲和二叔莫属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,父亲当年能做得一手好“硬菜”,他会用同一块猪肉,根据搭配食材的选用,分别做出“梅干”“夹夹扣”“磅”“粉蒸肉”“珍珠榨”等几种扣肉以及“黄肉”(糖焖肉丁)等等。为了能赶在年夜饭之前把这些菜做熟,父亲会从上午开始就一直值守在灶房里,因为做这些菜时,需要将它们分层置于一个大竹蒸笼里隔水蒸熟,这个过程所需要时间较长,而且还得保持灶膛里的火候一直是旺着的,如果稍有火力疲软,蒸笼里的蒸汽就不足,要么会使这些菜蒸不熟,要么就会“回汽水”浸进菜碗里,使得菜品质量下降。

说二叔是做年夜饭的第二把能手,他的功夫不在做菜方面,而是在宰杀鸡鱼及用大木甄蒸饭方面。整个大家庭大大小小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起,这样的大锅饭可不是好煮的,同时这杀鸡宰鱼的活儿自然就落到二叔的手中,他一边在另一口大锅上煮着饭,一边腾出手来做第二个“屠户”宰杀生鲜。
父亲熬浆贴春联的那个泥炉此时也被奶奶和二婶利用起来,在母亲和小婶的配合下,主要用于家常菜的烹煮煎炒。至今还回味奶奶用酸辣椒炒的鸡杂,以及二婶用“窖水”(制作豆腐时滤取的汁液)直接煮成的青菜豆腐,前者代表着沉香厚重,后者表达出清清白白,都蕴含着最朴实无华的处世哲学,会感染着人生。
大约在下午四时左右,由大家庭中所有人参与的年夜饭制作接近尾声,我们几个孩子去堂屋里布置三四方桌凳,然后叽叽喳喳地吆喝着快上菜。于是二叔、二婶分别用两个“茶盆”从灶房里将菜端来满满地摆上几桌,盛宴即将开启——有一种馋,叫做年夜饭。

堂屋“香盒”(供奉祖先的神龛)下的那张大八仙桌上能上座的,一定是整个大家庭中最德高望重或辈分高的人,自是该由奶奶坐上席,然后是父亲、二叔、小叔左右相陪,再然后是母亲、二婶、小婶依序下席相坐。开吃前,还有两个仪式需要举行,一是焚香燃纸照烛放鞭炮祭祖,这个仪式多由二叔主持,他把香纸烛燃起来之后,会去敲一下放置在神龛上的一个磬,据说这是向去了那头的先人们“发信息”,请他们来“吃”年夜饭。

另一个仪式是在堂屋八仙桌前铺上一件蓑衣,按照家庭中到场人员的辈分及年龄长幼顺序,轮换地坐在正位上,接受也按辈分年龄递减下来的人逐一磕头致祝福。
当所有的繁缛都终于消停之后,年夜饭才真正地开吃了,尽管满桌的菜肴已经有些凉了,但一大家子却吃得津津有味,其乐融融……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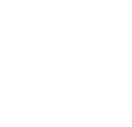

作者简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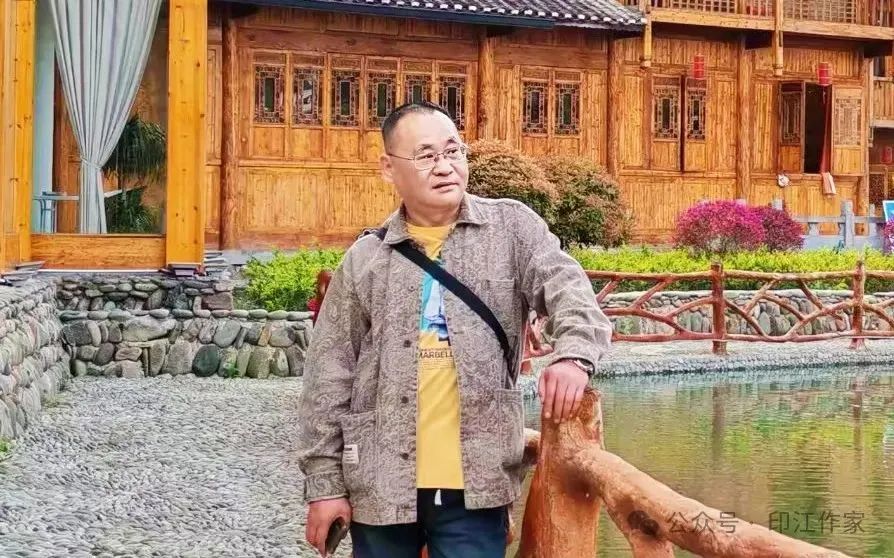


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吴霞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吴霞



